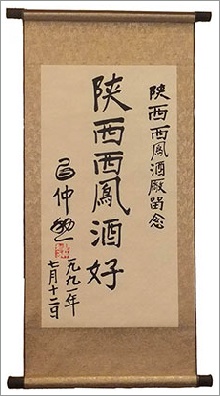
【西鳳酒1952報道】去年歲末,在陳升一年一度跨年演唱會即將鳴鑼前,聽到新寶島康樂隊的《第狗張》,真是不小驚喜,嘆服大叔的心力、體力、精力充沛如斯,唱歌就像說話那樣自然輕松,張口就來,寫歌就像寫信一樣自由自在,隨隨便便就打動人。有人問,這種十年如一日的“輕松”心態是怎么煉成的,難道用大而不當的“才華”兩字就可形容?
青年時可以用熱愛來保鮮才華,年歲增長,更多時候就要把唱歌當成一種生活,而不是一份吃飯的職業,唱出來的歌就是活的,才有人間煙火味。沿襲新寶島康樂隊傳統,《第狗張》繼續是一張講民間“故事”的專輯,對眼前的事物保持了新鮮感,唱出來就是故事。第一首《蟾蜍姑娘》翻唱自澳大利亞樂團The seekers的《Georgy Girl》,悠閑的口哨一出場就拉近距離。
用方言演唱看似在縮小聽眾的范圍,自動刪選了一批聽眾,另一方面卻是擴大了表達的路徑,描摹日常境遇,身邊小人物、小事件,可以遵從潛意識,用習慣性日常用語敘述,直白率性,讓懂這個方言的人一聽,馬上心領神會,莞爾一笑。所以,當陳升唱國語時,是在唱家、國,用正統國語寫歌,是唱片工業下的藝人。用方言唱歌時,就是在唱鄉土小人物,口白落落,像當街賣唱的歌手。
陳升寫的《吊蝦仔》,包涵了呵斥、質詢、勸誡的語氣,一長串排比句型,都是口語化的字眼,如果換成國語書寫,味道就要打折扣了。黃連煜的《我的情妹啊》,顯然是借鑒了傳統的閩南情歌,月白清風佳人有約的土地和莊稼的氣息,自然環保不失可愛。《應該是柴油的》屬于政治諷刺和民生關懷,開場卻是歌舞升平煞是熱鬧,陳升的小狡黠、小幽默,像一個鄉間老漢的口吻。
這兩年大陸觀眾詬病中國電影的一個說法是缺“地氣”,其實不僅是電影圈,音樂圈也差不多,小時髦和小清新齊飛,無視現實與不關心內心共存。陳升和新寶島康樂隊唱了二十多年不倒,正是得益于島嶼的自然心態純正地氣,在松散的心境下寫寫唱唱,茶酒詩畫放眼都是細節,以一顆平常心生活在這片土地上,一下筆、一開口,熟悉的人事就被賦予了街坊鄰居一樣的熟稔和人情。《光明戲院》是擁有四十多年歷史的老戲院,因為票價低,空間大,周遭有熱鬧小集市,印證了很多人的青年時光,這首歌既是挽歌,也是墓志銘。就像蔡明亮電影《不散》里的那種人跡寥寥的老戲院,而今終于因為擋不住拆遷步伐,改建成商業社區迫在眉睫。《美瑤村》還是寫人,為紀念剛逝世的著名演員張美瑤。
《一個人的生活》、《高士村》、《走到這唱歌》、《原住民的演唱會》對排灣族等原住民音樂的采樣和引用,幽默深情,自嘲且熱鬧,聽著很新鮮,讓專輯的音樂走向不僅限于平原上的閩南語,延伸到山地民族群落,窺視生于斯長于斯的命運和權益,以及在商業侵蝕中保持自我特質的愿望。
去年新寶島康樂隊《腳開開》出來時,就感嘆陳升的才情和精力,夏天才推出二人組合專輯,年底就推出了《家在北極村》。今年底又有這張《第狗張》問世,陳升和新寶島康樂隊真把唱歌當成吃喝拉撒一樣的簡單事情了,既要認真面對,又要放輕松投入,不圖名圖利,張弛有度,施施然享受其間,就像樂隊的名稱,《第狗張》專輯兼具康體、娛樂的效用了。
以上文章均來源互聯網,著作權歸作者本人所有,如有冒犯請聯系刪除.

